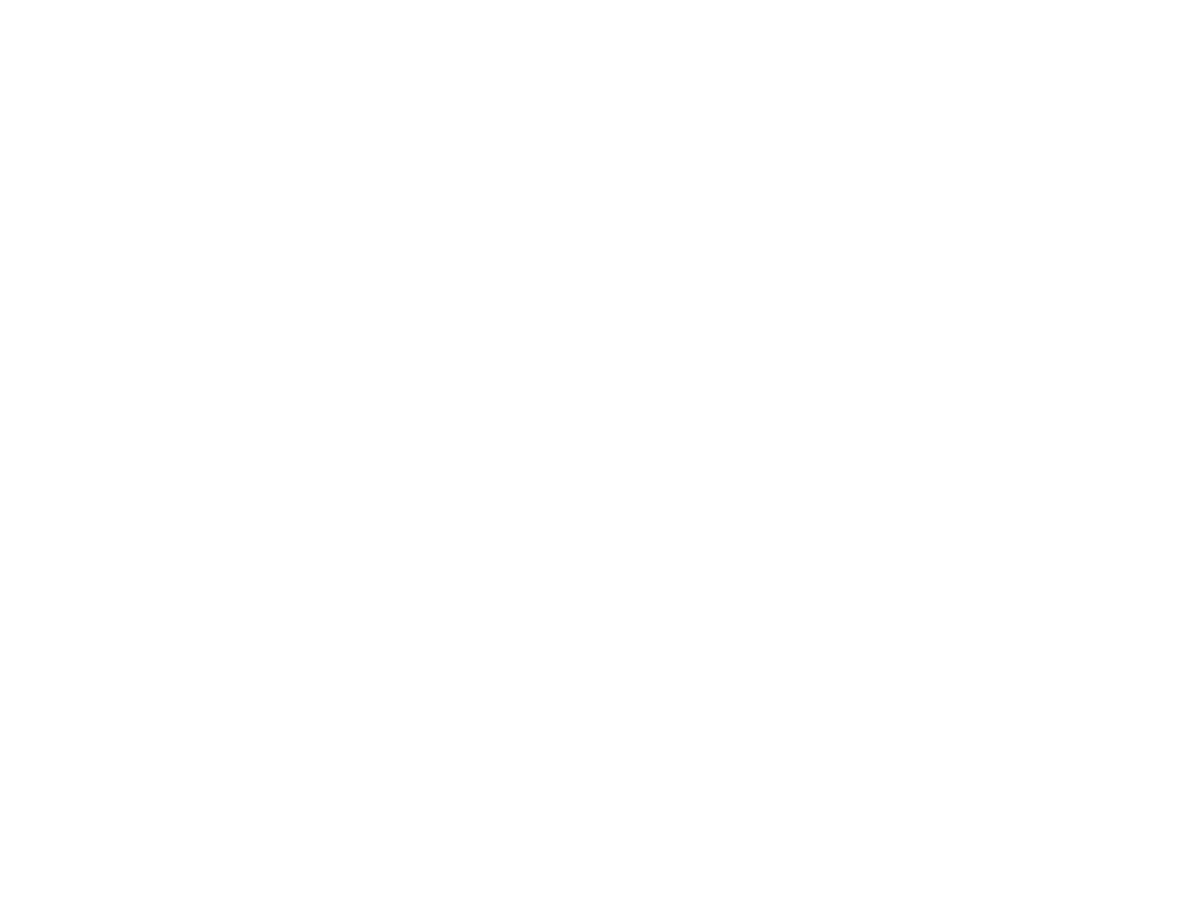佐治敬三憑藉著過人的行銷才能,在一波波的行銷操作中將三得利的品牌深植人心 (見:「承先啟後,匠心無限:佐治敬三的三得利之路 (上) 國內市場的持續深耕」);1973年,他更於山梨縣北杜市的南阿爾卑斯山脈中,興建了被譽為「森林中的蒸溜所」的白州蒸餾所,釀製工藝上的精益求精與不斷探索創新,為三得利威士忌帶來了獨特且多樣的風貌(見:「承先啟後,匠心無限:佐治敬三的三得利之路 (中) 白州蒸餾所」)。然而,國際化的願景始終是他威士忌商業藍圖中的重要部分。
與國際接軌
日本單一麥芽威士忌的誕生
 (圖片來源:羅芙奧尊釀雲集藏酒拍賣)
(圖片來源:羅芙奧尊釀雲集藏酒拍賣)
鳥井信治郎專注於本土市場,為三得利打下堅實穩固的基礎。而隨著三得利威士忌在日本的成功,佐治敬三則放眼國際,他深信日本威士忌不應只侷限在國內市場,應該要讓世界見證他的卓越與獨特。
1984年正值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巔峰,也是調和威士忌市場蓬勃發展之時,佐治敬三大膽地推出「山崎」單一麥芽威士忌。希望透過本土蒸餾釀製的單一麥芽威士忌,展現日本得天獨厚的風土條件、職人們極致的蒸餾釀造技術,以及所孕育出的威士忌那獨到的內斂優雅。
然而,單一麥芽威士忌並非一推出便廣受歡迎。1984年之後不久,日本經濟開始陷入長期低潮,日本威士忌產業步入寒冬;而蘇格蘭威士忌也在同一時期面臨著自七零年代黃金時期轉入產量過剩、供過於求的狀態,許多酒廠陷入停產甚至倒閉的窘境。幸而在這樣艱難的市場環境下,我們觀察到單一麥芽威士忌如黑暗中的一絲曙光,逐步在調和威士忌的式微中嶄露頭角。「單一麥芽威士忌」這個概念很早就存在於裝瓶廠的作品當中,格蘭菲迪更是早在1963年便率先以單一麥芽做為品牌訴求,但一直要到1980年代,DCL的Malt Cellar Collection和United Distillers推出的Classic Malts of Scotland意外受到市場熱烈迴響,單一麥芽威士忌這才逐漸受到蒸餾廠的重視。隨後在2000年代初期,單一麥芽威士忌逐漸從一個極小眾市場走向國際舞台,受到對高品質有所追求的消費者的青睞。山崎12年自1984年推出後,也一直要到2003年才開始在國際烈酒競賽中屢次獲獎。正是因為山崎和後來1994年白州單一麥芽威士忌的陸續問世,讓日本威士忌有機會站上世界威士忌的舞台,開創了日本威士忌的全球化時代,再再證明佐治敬三於1984年的決策展現了他前瞻性的市場眼光。
集大成之作—「響」的誕生
 (圖片來源:羅芙奧尊釀雲集藏酒拍賣)
(圖片來源:羅芙奧尊釀雲集藏酒拍賣)
1989年正值三得利創業九十週年,佐治敬三希望能推出一款「用日本人的手,打造出的世界級日本威士忌」,向父親鳥井信治郎一生懸命的堅持致敬。
在時任首席調酒師的稻富孝一協助下,他們從三得利旗下的兩座麥芽蒸餾廠—山崎與白州、以及專注於穀物威士忌的知多蒸餾所中,挑選超過三十種酒齡17年以上的威士忌原酒進行調配。鍾情於交響樂的第二代首席調酒師稻富孝一在調製「響Hibiki」時,布拉姆斯第一號交響曲第四樂章盤旋心中,奠定了響燦爛奢華卻又和諧的獨特風格。
「響」可以說是佐治敬三自1961年接掌三得利後兢兢業業的縮影。集旗下三個蒸餾廠最精華的酒液,將三得利豐富的釀酒歷史凝聚在一瓶威士忌當中;而刻意採用超過三十種以上原酒的調和,部分酒液於日本特有的水楢桶中熟成,打造出的酒液有著獨特的日本神社線香風情,是西方世界難以想像亦無法模仿的東方風格,可以說是日本調和工藝的極致展現。在包裝上,向來擅於行銷的佐治敬三也毫不馬乎,瓶身標誌性的24道切割面,更寓意著24節氣的更迭,代表響系列經時間淬煉的風情,也呼應著三得利的品牌精神:強調人與自然、自然與社會的和諧共鳴;酒標則採用來自京都堀木エリ子工作室的越前和紙,由書法家荻野丹雪題字,將日本職人工藝完美融入。

響(Hibiki)一系列的酒標是委託堀木エリ子(Eriko Horiki)和紙工作坊所生產。
エリ子表示和紙的日文讀音與神(かみ)相同,他具有一種能量、一種意義、一種精神,和紙蘊藏著含蓄的力量,代表著純淨與穩定。
來到位於京都的工作室,這才發現原來和紙有這麼多的可能性,他可以融入建築成為建築物的一部分,作為牆壁、天井、柱子、甚至是大門;也可以單純作為一件藝術品,成為空間中的亮點,例如屏風、隔間拉門、舞台背景……;他甚至可以在不倚靠任何黏著劑的狀態之下自成一件立體的裝飾品。和紙本身就有種低調的華麗感,而エリ子的作品能在不同的燈光與光線角度之下產生不同的光影變化,更是迷人至極。
 其實エリ子並非科班出身,但也正因如此,他的加入為和紙這個傳統產業帶來許多創新與突破,例如他利用紙天生容易破的缺陷,創造出布滿孔洞的和紙,讓缺陷變成藝術,讓不完美變得完美,也讓和紙展現出力量與脆弱間的張力。在與Dave Broom的訪談中,エリ子曾表示「對我來說,一方面是傳統,一方面是要做出適合今天的東西,工藝就是去了解這兩者之間固有的張力。另外也是尊重自然和生命,並且做出對某個人有價值的東西。」
其實エリ子並非科班出身,但也正因如此,他的加入為和紙這個傳統產業帶來許多創新與突破,例如他利用紙天生容易破的缺陷,創造出布滿孔洞的和紙,讓缺陷變成藝術,讓不完美變得完美,也讓和紙展現出力量與脆弱間的張力。在與Dave Broom的訪談中,エリ子曾表示「對我來說,一方面是傳統,一方面是要做出適合今天的東西,工藝就是去了解這兩者之間固有的張力。另外也是尊重自然和生命,並且做出對某個人有價值的東西。」
不過,要創造出這種美麗和諧的光影變化,實際上是必須經過精心設計的。工作坊裡的和紙平均尺寸為270公分*210公分,由於面積龐大,需要超過10位工匠同時作業,小小的差異會在這之間產生,因此他們會說70%的設計、30%的隨機,每一張的和紙都是獨一無二的。
 (2024年,三得利發表了響截至目前的最高年份– 響40年。)
(2024年,三得利發表了響截至目前的最高年份– 響40年。)
三得利的利益三分主義
1961年,佐治敬三創立了三得利美術館。一開始設址於千代田丸之內的皇宮大廈(パレスビル),2007年搬遷至如今的六本木東京中城(Tokyo Midtown)三樓與四樓,空間由日本建築大師隈研吾設計,融合日本傳統風格與現代線條。三得利美術館以「生活中的美」為宗旨,館藏包含茶道道具、漆器、織染、陶瓷、繪畫與日本古美術,向世人展示日本文化的深厚底蘊。
 (照片來源:The House of Suntory)
(照片來源:The House of Suntory)
而為慶祝三得利威士忌六十週年與進軍啤酒二十週年,佐治敬三參與了六本木與赤阪交界處的ARK Hills (アークヒルズ)重建計畫,並斥資興建了三得利音樂廳(Suntory Hall)。音樂廳於1986年啟用,是日本首座專門為古典音樂設計的大型音樂廳,由指揮界的傳奇人物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擔任顧問、並由永田音響傳奇的聲學工程師豊田泰久設計,三得利音樂廳憑著一流的音響效果擠身世界著名音樂廳之列,如今,三得利音樂廳已成為世界頂級樂團與古典音樂大師亞洲巡演必訪的一站。
 (照片來源:Suntory Hall官方網站)
(照片來源:Suntory Hall官方網站)
鳥井信治郎堅信,商業能夠成功,依賴的是社會的支持,因此回饋社會是企業的職責。佐治敬三繼承了此一精神。他相信,企業的存在不僅僅是生產與銷售,也不能僅僅是追求生產目標與數字,更應認真思考能夠為社會提供何種價值。正是這種觀點,使得三得利的文化事業與社會貢獻延續至今,這是三得利企業精神的核心,也為三得利注入深厚的文化內涵。
 (Suntory Hall於1986年10月12日開幕,創辦人佐治敬三在管風琴上按下A鍵。
(Suntory Hall於1986年10月12日開幕,創辦人佐治敬三在管風琴上按下A鍵。
圖片來源:Suntory官方網站)
傳承是過去的創新,而創新就是未來的傳承。日本職人精神講求的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傳統,他們勇敢順應當下的市場,擁抱改變,不害怕失敗也不輕言放棄,如果一定要用一個形容詞來定義日本威士忌,「永不放棄」的日本職人精神,或許就是最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