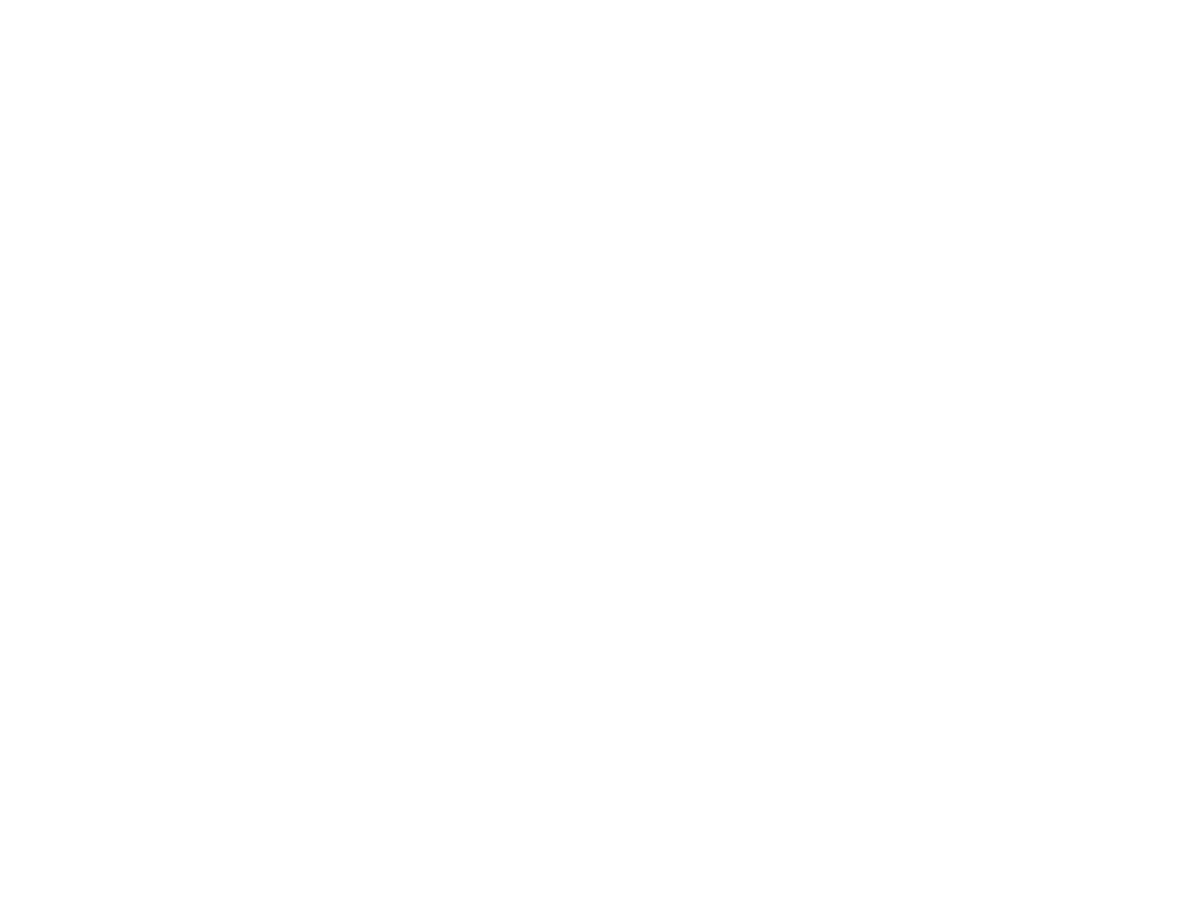十月初到香港了參加了Wine Fraud舉辦的葡萄酒鑒定課程,培訓課程的主講人是被業界稱為「葡萄酒福爾摩斯」的Maureen Downey。Maureen自2005年起便致力於辯證葡萄酒的真偽,如同電影《酸葡萄 Sour Grapes》所述,Maureen作為協助破案的一員,她協助著全世界各地的藏家釐清自己收藏的正確性,親自站在法庭第一線打擊假酒,如今更在世界各地建立葡萄酒鑑定軍團,是假酒鑒定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
Maureen相信,葡萄酒的生產是一個專業的流程,儘管我們認為法國人生性浪漫,但對酒質有所追求的莊主們不會放任玻璃瓶、酒標印刷、酒塞選用等細節的隨意。
透過訓練課程,我們了解在某些情況之下,假酒確實很容易被識別,舉例來說,GUANGDONG-CONTI這類明顯的拼寫錯誤、聖彼得被換置成毛澤東頭像的Petrus等酒莊標誌的誤植、寫著Bordeaux的Sassicaia等產區資訊的謬誤……,然而,手法精良的仿冒品有的使用回收空瓶、有的重複利用舊酒標,使得具體判斷變得益發困難,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敏銳的雙眼,更需要長時間經驗和資料庫的累積。

(Photo courtesy of winehog.org)
樸實且枯燥的驗酒過程—九十五個檢驗點的把關
Maureen和她的專業鑑識團隊建立起了一套有著95個檢驗點的系統驗酒流程,大項目包含了酒標、錫封、玻璃瓶、印刷、墨水、膠水、酒塞,酒標大項內又包含了彩色圖樣、文字印刷、老化狀態、髒污破損程度等細節,每一個項目的比重不同,但都必須被考慮,且每一個細節都必須相互呼應。這樣的程序跑下來,一瓶酒的檢驗至少需要20分鐘,Maureen和她的團隊在過去二十年便是這樣,在全世界各地的酒窖中不斷重複著九十五個檢驗點的流程,累積出數十萬筆的資料庫與輝煌的戰績。
在所有的線索中,Maureen認為酒標的紙張、印刷方式、墨水的使用等,個別拆開或許都不是太過困難,但疊加在一起,便是對造假者的考驗。最最基本的是酒標圖案的紋理必須要清晰,套句Maureen的話:「沒有人會把自家酒廠的標誌印得模糊不清」,所以在放大鏡下,我們應該期待Lafite酒標上女人的臉龐和男人衣服線條分明、Haut Brion建築物上每個窗戶線條分明、Henri Jayer的家徽盾牌線條整齊且雄獅爪子清晰可見、Armand Rousseau的紅色和金色色塊色澤飽滿……。
真實的歲月痕跡
此外,人會隨著時光的流逝而逐漸變老,紙張也是,它會隨著陳年而沾染上歲月的痕跡。若遇上一瓶酒標嶄新的老年份酒款,除了探詢酒莊近年新釋出(late release/ new release)與重新整理(recork)的可能性,也得思考我們是否不幸碰上了位整形成18歲少女的80歲老嫗。
根據FBI從Rudy家中搜出的製假道具,發現他會利用烘烤將紙張烤得泛黃、利用咖啡漬、酒漬或菸草將乾淨的新酒標弄髒、甚或故意將酒標弄破,讓人們相信酒的老舊。然而大量製造的泛黃酒標由於彼此重疊,往往可以從異常規則的線條中找到線索;咖啡、酒等液體帶來的髒汙竟奇異地沒有任何液體自然流動的痕跡、或從破裂的酒標下方出現溢出的膠水痕跡……等,儘管存在障眼法,對於經驗老道的人來說仍然有著許多破綻。
酒液本身當然也是會隨年紀而逐漸老化的,他們的顏色會漸漸變淡,酒渣也隨著年齡而變多,蘇富比的葡萄酒專家Serena Sutcliffe就曾說,真正的老年份葡萄酒不應該是強勁或活躍的,不會老化的只有那些做過整形手術的怪物。酒渣(sediment)就是Maureen鑑定團隊九十五個檢驗點的其中一項。

(Wine labels used as evidence in the trial of wine dealer Rudy Kurniawan. Photo: AFP)
知識就是力量
辯證真酒假酒需要的除了無比的耐心和經驗,也必須要有過人一等的記憶力和足夠的知識。
如果知道Pauillac AOC制度是在1936年才建立,當看到一瓶掛著Pauillac AOC產區規範的1821年Château Lafite,第一反應就會從讚嘆轉為嘆息;如果知道Rothschild家族在1868年後才擁有Château Mouton,看到一瓶1859年Château Mouton Rothschild就不會盲目地追求;如果知道五公升瓶自1978年之後才出現在波爾多地區,翻閱到拍賣圖錄上一瓶1945年五公升裝的Cheval Blanc就該讓您心中警鈴大作。
熟悉各產區法規的生效日期與產區歷史、不同市場對於玻璃瓶使用的習慣、印刷技術的時代更跌、了解各酒莊們最新的防偽技術等,就算無法百分之百分辨出一瓶葡萄酒的真假,至少可以避免輕易陷入假酒誤區。
因被相信而存在的獨角獸
Maureen Downey一次又一次在公開場合強調,當一瓶酒的來歷與故事越精彩,通常就越有問題。舉例來說,當有人試圖向您販售一瓶僅存在酒莊內從不曾對外發售的1945年大瓶裝DRC Romanée-Conti、深埋在比利時某神秘家族酒窖中的十六世紀 Château Lafite,心中的警報就必須拉響。正如同Rudy所創造的1945年 Domaine Ponsot Clos Saint Denis,Ponsot家族直到1982年才開始這塊葡萄園的生產,這種類型的假酒通常利用了人們對於「獨角獸」那獨一無二、界於現實與幻想間浪漫的迷戀。
從聞「假」色變 — 假酒問題有多嚴重?一文我們已經知道假酒確實是個需要被高度重視的課題,且只要有利可圖,仿冒就不會停止,即便Maureen Downey、Michael Egan、Jancis Robinson這樣的專業鑑定大師堅定地站在第一線,能做到的防範依然只是杯水車薪。正如曾被Rudy假酒殃及的倫敦佳士得拍場負責人所說,防治假酒需要的是整個葡萄酒產業鏈的重視,專家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便是呼籲大家正視問題,不要覺得買到假酒是羞於啟齒的事情。
熱愛葡萄酒的我們,同樣也不需要因為假酒問題的氾濫而因噎廢食,我們能做的,是找尋自己熟悉且信任的購買渠道,不要貪小便宜,並且不斷的自我充實,如此,不僅能減低落入仿冒者陷阱的風險,也能在深入了解一瓶酒的來歷與背景之下,領略這瓶酒的獨特、享受它所帶來那無與倫比的體驗。